隐于《顾颉刚日记》背后的“打工人”汪安之
- 商业
- 2024-10-03 13:32:25
- 10
顾颉刚(1893-1980)的好友傅斯年曾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日记、书札等作为第一手资料,素来为现当代学者所重视,尤其近年来对未刊的日记、书札手稿的整理,伴随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中国近代日记丛刊》《晚清珍稀稿本日记》《现代学人日记丛书》等几种丛书的出版,俨然出现了一个高峰。最近,张剑兄《近些年日记整理情况与未来展望》一文(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4年第4期)对日记的整理、出版情况,作了简明扼要地梳理,值得一读。
2007年、2011年《顾颉刚日记》先后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后,因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众多、记录简明,甫一出版便成为海内外研究近代学术史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余英时曾专门为联经版《日记》写过长序,真的很长,长到可以出单行本,那便是《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在序言中,余英时揭示了顾颉刚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这源于他对《日记》的细致阅读、深入挖掘。《顾颉刚日记》固然是可作信史读的,却也有一些被我们忽视的地方。在此,只是想用一个与《顾颉刚日记》相关的小人物——汪安之作为例子,对日记材料做一个抽样式的分析,揭示一些隐于《顾颉刚日记》背后的细节。

顾颉刚
一、发现汪国治
汪国治就是顾颉刚的表弟汪安之。汪安之在《顾颉刚日记》中出现得并不多,甚至他的大名“汪国治”一次都没出现过。虽然他曾参与南京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疆》杂志的相关事务工作,但并不从事学术研究,就是一个普通“打工人”,且为期颇为短暂,故顾潮在《顾颉刚年谱》谈及中国边疆学会时,汪氏名字一次都未曾出现。《顾颉刚书信集》中,也没有收录致汪氏信函。幸好汪安之的日记残留了一部分,让我们在六七十年后,重新发现顾颉刚这位略带神经质的汪家表弟。
《汪安之日记》稿本四册,是我在苏州博物馆资料部日常编目过程中自杂件库理出,后来将之编入《苏州博物馆晚清名人日记稿本丛刊》影印出版。原稿四册,为民国三十六年第二、三、四、五册,缺第一册,有些可惜。四册书衣单题“日记”,并不署名,仅钤“汪国治印”,只知作者是汪国治。纪事始于1947年5月28日,终于1948年1月20日。在日记第二册的夹层中发现了两通顾颉刚的书札,确认汪国治就是汪安之的大名。两通书札,我已在《偶见“双哥”遗简》(收入拙著《春水集》)一文中作了介绍,并示俞国林兄,内容得以收入《顾颉刚全集补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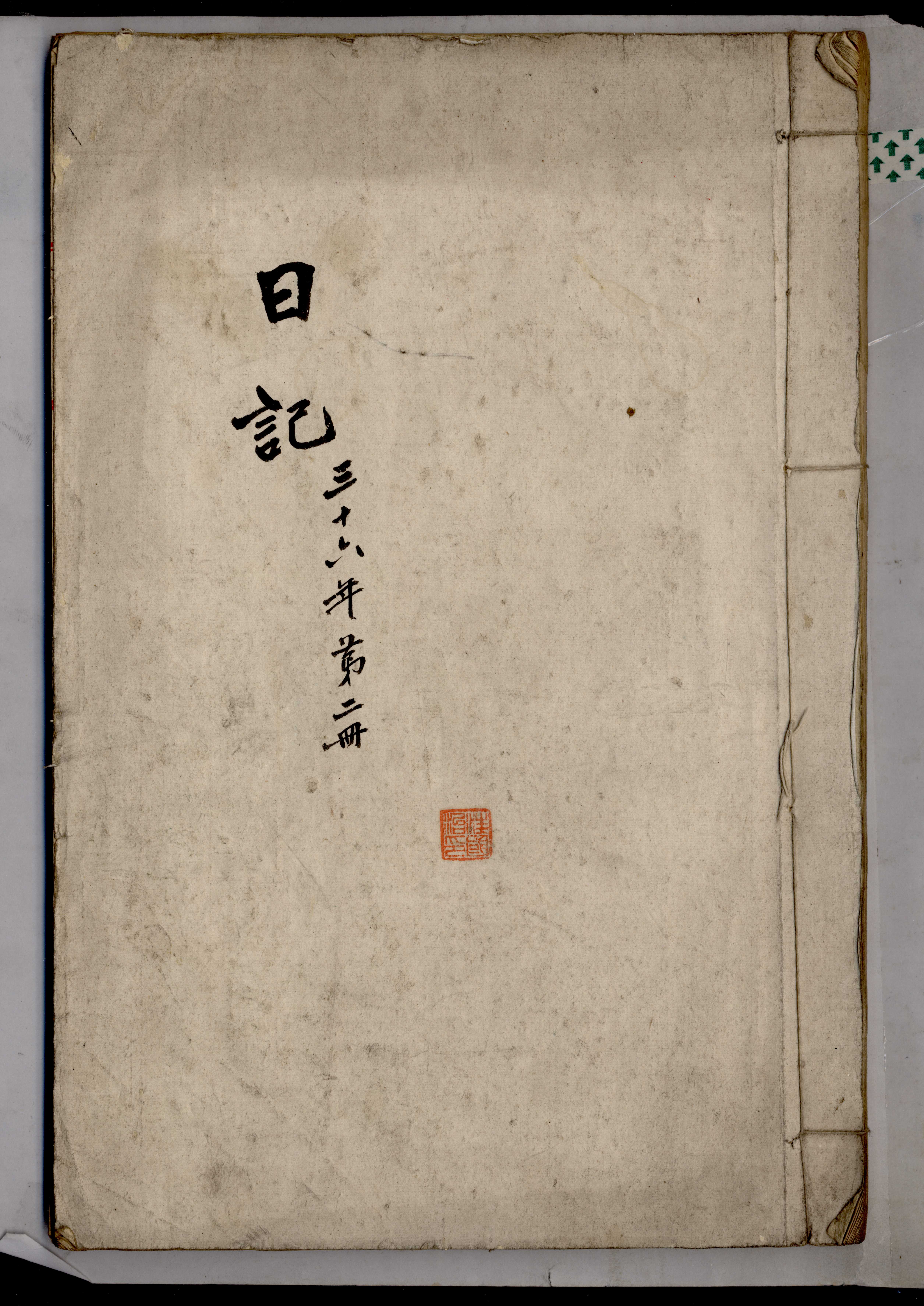
有关汪安之的家世情况,从他本人的《日记》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47年8-9月间,汪氏因手臂生病回苏州休养,曾去胥门外王家村展拜“迁吴七世祖廷臣府君,六世祖静安府君及五世祖介堂府君”,闲暇时整理祖先传记,9月11日曾撰写《先祖考凌皋府君传》,他父亲则去世已达十五年之久。由此可知,汪安之的祖父应该就是吴县汪鹤衢(1840-?,字青昂,号凌皋),同治九年(1870)举人,光绪七年(1881)后历官常州府、太仓州训导。他们这一支汪氏,同样祖籍安徽歙县,由歙县迁休宁后,再迁苏州,世居盘门梅家桥,故称梅家桥汪氏。同族中,清末曾出过秀才汪芑(1830-1889)、举人汪钟霖(1867-1933)等。据1947年8月23日黄奋生致汪安之函,信封地址开“苏州盘门西大街七十一号”,知其当时住在盘门内的西大街。
汪安之的母亲与顾颉刚之母是同父异母的姊妹,汪安之第一次在《顾颉刚日记》中出现,便是1933年7月11日和汪姨母一同找顾颉刚,“商讼事”。彼时,汪安之三十六岁,尚未成家;顾颉刚已四十一岁,处事十分干练。两人年龄相差五岁,表兄弟间相当亲密,1933年8月20日顾颉刚还曾“为安之弟写扇”。
1946年5月,顾颉刚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苏州。汪母于1944年7月去世,汪安之已四十岁出头,依然单身未婚,待业在家。在《顾颉刚日记》中,1946年5月29日有“汪安之偕其妹三人来”的记录。同年11月6日有提到“到医院。二婶、九婶、吴子明太太、三侄女、余妹到院视静秋,汪安之兄妹三人亦来,同游拙政园”。12月11日,顾颉刚为父亲及亡妻殷履安安灵设奠,来客名单中有汪安之。
因有表亲这层关系,1947年,顾颉刚将待业在家的大龄单身男青年汪安之推荐到南京中国边疆学会工作,可以说解决了表弟的燃眉之急。当日,中国边疆学会借用新亚细亚学会位于南京江苏路八号的场地,汪安之落脚于此,寄人篱下。中国边疆学会也因为汪安之的到来,成为顾颉刚在南京的临时办事处,他到南京开会,必到边疆学会,了解相关工作;他去陪张静秋去徐州,一般从苏州出发,都会在南京停留一晚,次日过江换车北上,汪安之也会帮忙照应。
1947年6月6日,张静秋自苏州去徐州,中途在宁停留一晚。顾颉刚正好在南京开会,《日记》有饭后“乘人力车到站,则凯旋号车早到。到边疆学会,留条,回旅馆,则静秋等已来,由起釪接得”的记录。其实,这一天顾颉刚上、下午先后两次到过边疆学会,汪氏中午也曾抱病往下关站接表嫂,结果火车提前到站,张静秋由刘起釪接走了,他在日记中对此记录甚详:
午前,双哥来会,告悉表嫂今日十四时左右来京小住去徐,带有行李。下午,面症不甚痛,因乘车去下关车站。迨询得苏州来车时间已过,即折赴鼓楼医院,就诊面症。归,又得留条,知双哥亦以时间相左,未能会面。晚饭前,邮局送到致双哥信,按之觉颇厚,或有重要事,饭后即送去,则表嫂等已至逆旅矣。略道家常,匆匆即返,时计已过九时焉。迨抵会,又见桌上教育部致双哥至急函二件,乃嘱工役乘车送去。
隔天晚上,汪安之去给顾颉刚送信,考虑到张静秋一人孤身赴徐州,又专门买了面包、橘子露等送去中央饭店,“俾表嫂车上之需”,从点滴细节中,可见他并不是一个不通人情之辈。不过,亲友口中称道的“自家人”,未必是一个好的“打工人”。
二、“老板”眼中的“打工人”
在南京中国边疆学会工作期间,汪安之满眼都是表兄顾颉刚,而顾颉刚似乎并不十分欣赏这位表弟,尤其是在离职风波中,他作了一段评价,像领导写的工作考核一般,这在后文会细说。客观说来,汪安之是个感性的人,所以有时会神经兮兮,顾颉刚是理性的学者与管理者——今人研究学术史,特重学者气质,而忽视其管理者身份,试想顾颉刚没有一定的管理能力,何以能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如果去掉表亲这层关系,当时汪安之与顾颉刚之间,确存在上、下级关系,虽然不像现今的老板与员工那般,但也不可无视。边疆学会工作尽管琐碎繁杂,头绪无数,汪安之尽力做好,对顾颉刚负责。不过,边疆学会工作却只是顾颉刚所有工作的一小项,他接触的人与事是汪氏的十倍、百倍之多。从这个角度,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汪安之日记》里满是顾颉刚,反之《顾颉刚日记》里很少提到汪安之。
1947年5月中旬,顾颉刚到南京开会,为期近一月,两人日记的时空第一次出现重合。5月19日上午七点三刻,顾颉刚乘火车从苏州赴宁,参加参政会,当天下午两点抵达南京,他与邵力子夫人同乘汽车到会报到,取款携物,入住中央饭店二一九号。随后毫无意外,“到边疆学会,晤公武,安之”。安之即汪国治,公武即许崇灏(1882-1959),系许崇智、许广平的堂兄,新亚细亚学会的负责人,也喜研究边疆史,著有《新疆志略》《琼崖志略》《青海志略》《内蒙古地理》等。当时南京的中国边疆学会借用新亚细亚学会的地方办公,这直接为后来汪安之的“离职风波”埋下了隐患。

许崇灏
苏州博物馆藏《汪安之日记》始于1947年5月28日,当天就提到他去访表哥顾颉刚,结果未遇:
晨八时前,应黄君约,前去其住宅,面洽一是。午后,赴鼓楼邮局,寄成都陈宗祥稿酬若干元。晚饭已过,再去中央饭店,仍未晤双哥,恐迟误昨日收到大中国图书馆局函事,即留条及信,嘱值勤茶房转致。
黄君即黄奋生(1904-1960),江苏沛县人。顾颉刚与张静秋成婚,便由他和萧一山作伐。黄奋生与顾颉刚一起负责中国边疆学会事务,共同主编《中国边疆》杂志。显然,他也是汪安之在南京的领导之一,在汪氏日记中,时时要去黄处面洽会务,并帮黄氏跑腿。上文提到的陈宗祥(1919-2012),浙江宁波人,1940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哲心系,曾任教于华西协和大学、西南民族学院等校。1947年出版的《中国边疆》杂志第3卷第10期上刊发陈崇祥《宁属之水田民族》,汪氏所发稿费,或即此文之酬。反观5月28日这一天《顾颉刚日记》,并没出现汪安之的身影。
汪安之在边疆学会的工作普通而琐碎,包括但不限于收发稿件、草拟文件、发放稿费、邮寄样刊、寄卖刊物、采买物资,帮顾颉刚、黄奋生跑腿办事、收发信函等。如8月2日汪安之“早餐后即去太平路书店,计算《中国边疆》复一、二期销数,毫无起色,边疆问题不为国人注意也无疑”,唯有“感叹感叹”。尤其在联络基本靠通信的时代,每天都有帮顾颉刚转递信函的记录。顾颉刚在南京逗留这大半个月,他的信件都纷纷寄到中国边疆学会,均由汪氏处转交。《汪安之日记》提到,5月29日晚上,身在南京的黄奋生有一信致顾颉刚,也托汪安之转交,加上“上午上海朱姓致双哥函,于晚饭后送去。据云,双哥又外出”,于是仍交茶房转致。5月31日,汪安之又将信函四件,交工役送往顾颉刚下榻的中央饭店。6月10日“午前,双哥来。因下午应政治大学讲学之邀,嘱转致临时车迎地址而去。晚饭后,樊漱翁又来稍坐。然后送双哥函件,往返匆匆,将近十时数十分矣”。可见汪安之对待这份枯燥而琐碎的工作是十分认真的。6月13日,汪氏听说“颉刚表兄拟乘今夜十一时车去申后返苏,余乃于晨间前去中央饭店道别,并托带家信及国币十万元,妹等日前函示一是也”。《顾颉刚日记》用“安之来”三字概括之。
顾颉刚离开南京后,传递信函依然是汪安之的日常重点工作,如6月19日有“晚七时四十五分接到国史馆致颉刚表兄函,因即加封……快邮寄出”的记录,此后国史馆、立法会、教育部等致函,均由汪氏转寄。7月26日“国史馆致双哥函壹件,依日前双哥面嘱,拆阅一过,知系报告表壹件,因即平信转苏”。这些信件往来,《顾颉刚日记》中基本没有记录,自然也未提到为此奔波道途的汪安之。7月3日,顾颉刚写信给汪安之,嘱咐他固定每周写信一次,报告会中事务:
累承转信,至感。刚定本月九号到京,如再得他人来信,即不必寄下,待刚亲来领取。采妹有信,嘱转上,当届时面奉也。闻《中国边疆》第二期已出版,何以竟未寄下为念。此后每期可寄来五分,以便分发。会中事务亦望每星期作一报告寄刚,以便对人谈话时,不致隔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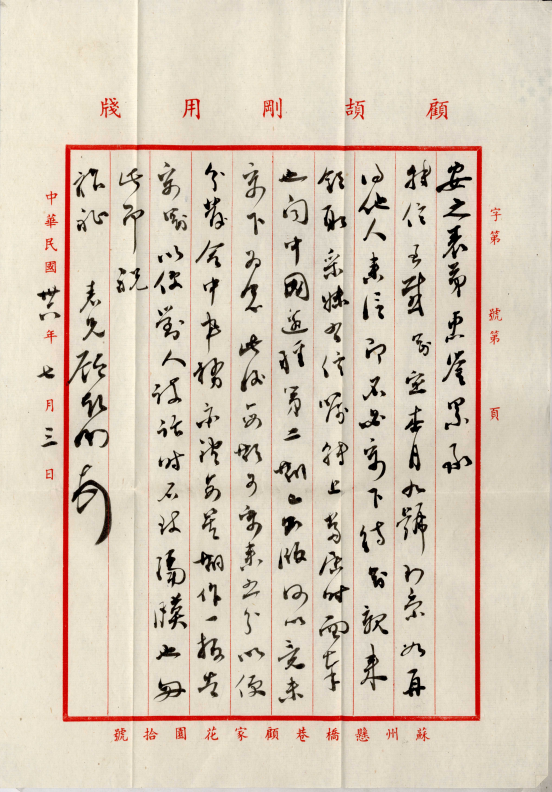
顾颉刚写信给汪安之的信
1947年7月9日上午八时半车,顾颉刚再次乘车赴南京,下午两点抵达,汪安之到下关车站接他,《顾颉刚日记》并未提及此事,只说晚上“到边疆学会,晤公武,安之,张西曼,取《民周》归”,汪氏日记则道出了不少细节:
午饭后,即去下关车站,候接双哥,恐行李褦襶,兼顾不易,要亦母党弟兄行应有之互助也。……晚饭后,双哥来会,带来妹等函,坐谈时许,并书就致王泽民函,明晨方可投邮矣。
在职场上,主动去给领导接站,会让人小小感动一下吧!汪安之确也这样做了,然却并非从职场角度考虑,而是沉浸在和“老板”的兄友弟恭中。虽然这个比方打得并不妥当,但可以肯定,顾颉刚与汪安之两人对此的看法可能并不完全一样。此后数天内——7月10日、12日、13日、14日(两次)、15日(送《民众周刊》一百册),汪安之均曾到顾颉刚宿舍寻表兄,像上次一样,大多数时间都没能见上面。直至17日下午五点左右,顾颉刚到边疆学会,告知汪安之将于当晚移居中央饭店三六一号房。从《顾颉刚日记》知,当晚他只是整理行李,次日才正式迁居。7月23日,顾颉刚即将离宁之际,汪安之“应双哥昨晚面约,即去中央饭店少坐,取到《民众周刊》赠余本若干。双哥偕余出外午饭,步出饭店,忽遇某君有事。余乃先与双哥握别,盖双哥拟今日下午三时余车赴沪转苏矣”。可能临别前,顾颉刚要从工作角度关照汪安之几句,一起吃顿饭,刚出中央饭店,就遇到别的事,只好匆匆告别。之后不久,汪安之的“离职风波”就来了,或许这早在顾颉刚预料之中,却直接导致了“打工人”的离职,间接也加重了他的癔症。
三、“打工人”的离职风波
汪安之到南京工作后,也在为自己的职业做规划。1947年7月中旬,汪安之对边疆学会的工作已经很熟练,他就打算参加上海昌明法政函授学校的函授课程,以期多条出路,于是向边疆学会提出预支薪水,以充学费,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惜,前文已经提到,中国边疆学会借用新亚细亚学会的场地办公、住宿,为汪安之的离职埋下了种子。究其原因,应是汪安之与新亚细亚学会的负责人许崇灏一家相处不甚融洽,以致最终关系破裂,汪安之无处安身,不得已“引退”。关于汪氏离职一事,在《顾颉刚日记》中没有太多涉及,只有寥寥几处汪安之到访的记录,实际上却一波三折,从汪安之本人的记录看,似乎他并未真正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就糊里糊涂主动离职了。
刚开始,汪安之与许家自然相安无事。1947年6月1日,许崇灏六十六岁生日,汪安之获悉后,专门略备薄礼相送,以为祝贺。许氏邀请顾颉刚参加寿宴,顾颉刚开会忙忘了,在《日记》中说“在碑亭巷吃饭。归,想起许公武生日,即赶往入席”,汪安之作为“打工人”却因此疲于奔命,他在日记中说:
许公老诞辰,余知焉晚,前去冠生园略购菲仪为赠,藉祝六六老人之添寿也。……午,颉刚表兄迟未来聚宴,黄君嘱电话以催。适由逆旅外出,未获通话。黄君又虞茶房传言不足凭,亟嘱去中央饭店面促。因再雇车往,茶房为余言,恰值赴宴中。力求确实计,仍留一字条,俾明余之来意也。
看《汪安之日记》,其中并没太多的笔墨谈及自己与许家的摩擦,更多的反而是与许家相处融洽的记录。如6月23日适逢端阳节,中午黄奋生邀汪安之去午饭,汪氏“再四言之,情不可却,应之。继思为余一人而诸多形扰,心实不安,因于午饭初过,即去其家,面致心领之忱”,足见他处世之法。晚上许公武“来邀叙餐,相处一楼,无辞可托,叨陪末座,杯尽大红——葡萄酒,为领主人盛情耳”,之后汪安之还写了两首七绝纪其事,即夹在日记中的《公老邀叙端阳晚宴》一页。
1947年8月中旬,汪安之手臂突又生病,在他请假回苏州一个多月后,回南京即与许公武发生冲突,一发不可收拾。从《汪安之日记》看,8月16日下午他曾去中央大学医院看手臂,“为详尽计,挂特别号”,结果医嘱开刀,他颇犹豫,找黄奋生商量,结果决定回苏州休养一段时间。8月19日,汪氏乘火车回苏州,归乡过程日记颇详细:
上午六时三十分,即乘公共汽车,至建康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旅行社,候启门,购得凯旋号车二等车票(二辆三十八号)一张,返会午餐。下午一时三十分,至下关站,二时三十分,进车厢对得号目,卸衣休息,四时三十五分启行。迨九时余抵苏,雇人力车至家已十时余矣。凯旋票已增至六万二千元。
次日,汪安之往顾家花园访顾颉刚,结果顾氏夫妇一早乘车赴徐州,失之交臂。其实,当天顾颉刚夫妇曾在南京逗留,顾氏并往边疆学会访汪安之,8月20日记有“予往访汪安之,未晤”的记录。
从8月19日回苏,一直到9月23日汪安之回南京,一个多月里,他听从妹妹的建议,用中医治疗手臂,颇见成效,但耗时颇久,曾两次写信给黄奋生,申请延长假期。病愈回南京的当天晚上,汪安之与许公武的矛盾就暴露了,《日记》载“返会,许公老嘱勿读夜书。余应之,并答以住的环境尚须调整,有何心思静读夜书,即日间亦无致力于此数日之可能”,次日因中秋临近,许公子和汪安之“谈送礼,余以为送礼一事,在交情上发生,否则即不适合人道”。仅仅一天之后,9月25日汪安之便提到“因会址迁移问题”去边疆教育馆一行,与黄奋生面商。黄氏建议他先回家几星期,“新址觅就后,通知来京”,汪氏未答应,接下来两天继续和黄氏沟通,无法一致解决。于是,汪安之决定直接去徐州“面告双哥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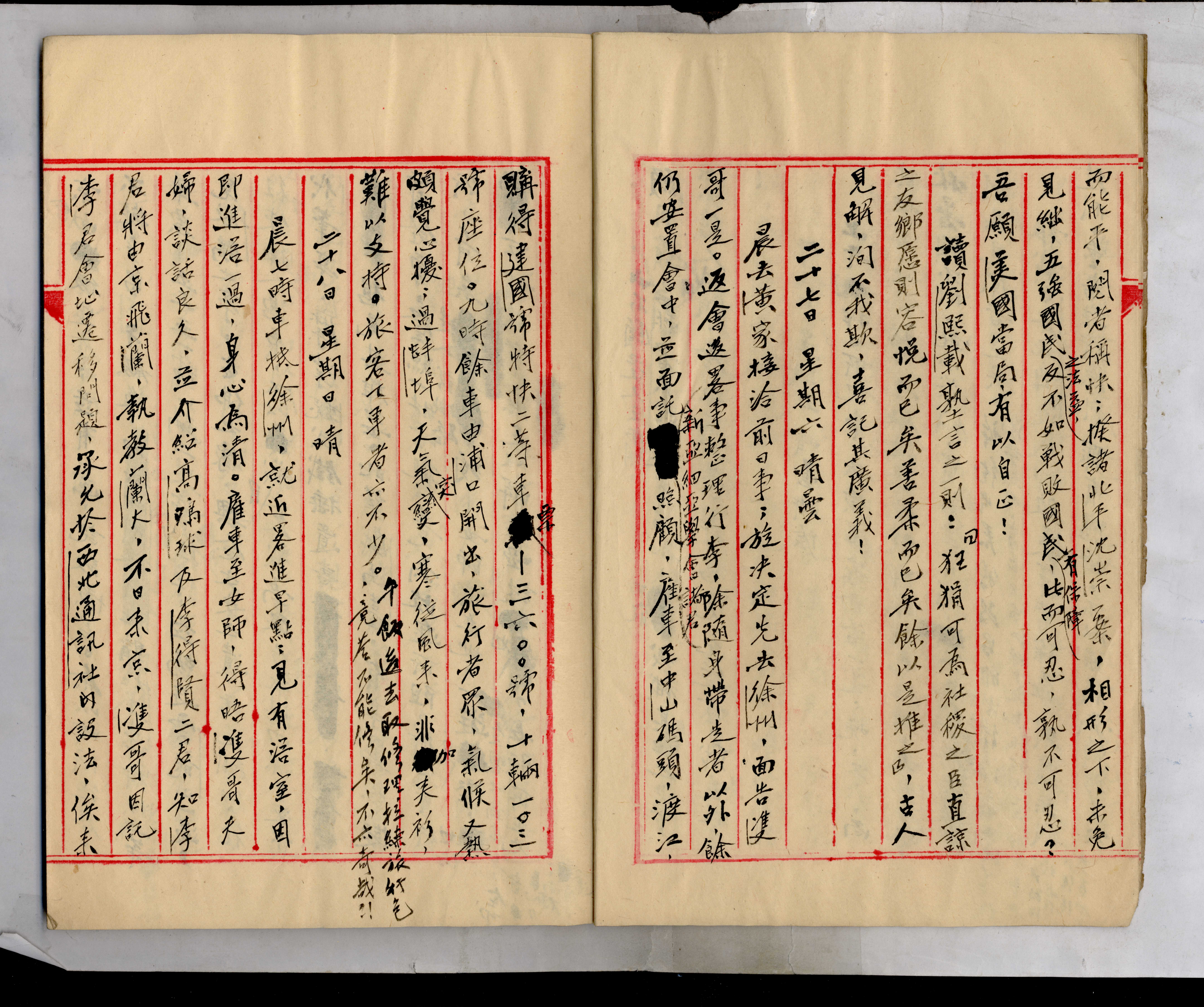
汪安之日记
9月27日,汪安之将会中事务略作安排后,“雇车至中山码头,渡江,购得建国号特快二等车”,晚上九点多开车,次日一早七点抵徐州,吃过早点、洗过澡之后,雇车到女师:
得晤双哥夫妇,谈话良久,并介绍高鸣球及李得贤二君,知李君将由京飞兰,执教兰大,不日来京,双哥因托李君会址迁移问题,承允于西北通讯社内设法,俟来京会面后定夺,并有一函,托致黄君。余以时间从容,不拟多留,午饭后,即去中国旅行社购和平号特快二等车票……并畅游云龙山一过。……晚饭后,与双哥、李君及车君等闲话,李君以学者而颇好相术,殆亦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之谓欤?八时余,雇车至车站,对号入座,九时十分南开。双哥病胃肠吸收力薄弱,以致时便时止,现倩某新医疗治,余以为此类病症,初以调养为主,旧医或更有效验方法,故力劝就旧医兼治,或口服资生丸,自可得到相当效果。双哥颇以为然。余乃戏语双哥,养病逍遥堂——东坡遗迹,自是受用事,相对莞尔。此行佳话也。
同一天《顾颉刚日记》,仅简单记了一句“汪安之自京来,商边疆学会事,晚回京”,关于南京中国边疆学会要迁址一事,顾颉刚特意附记了一段话:
安之以许公武先生与之不协,江苏路不能住,来想办法。因介文实之西北通讯社,不知能成事否。此人性太黏腻,接近神经病,为先母故,过而举之,实不慊也。
从中可知,汪安之此前在日记中说“以会务着想,自有迁址必要”,实际上迁址的主要原因是他本人与许家关系没处理好。
徐州之行,表面上似乎解决了边疆学会迁址的问题,其实不然。9月29日一早,汪安之回到南京后,连日数次往西北通讯社访李文实,想落实借用场地事,结果李氏未马上到宁。直到10月8日,李文实到南京,过访汪氏,言及“办公可借,而宿处不敷”,汪安之的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他在日记中感叹“适与黄君及双哥主张相反”,并说:
为今之计,尽力人事,不克如愿,唯有听其自然,可居则居,不可居则去,盖剥夺自由,毋宁自休,辜负双哥一番盛意,日内当预先去信言明原委也。
鉴于西北通讯社无法借用场地,顾颉刚、黄奋生都不可依靠,汪安之只能自己想办法。10月12日、13日,汪安之趁外出联络会中事务时,先后拜访吴佩庵、张礼千,均以宿处一事相托,不免有点病急乱投医。伴随住宿出现问题之后,汪氏还面临“饭食无处可包”的窘境,于是10月14日他自作主张,买了一副炊具,自炊自食,此举“竟触许公武之怒,不准煮饭”。次日,他从黄奋生家回到江苏路八号,发现炊具不见了,汪氏问许公子,“未及多言,许公武即来,声势汹汹,摩拳擦掌,大有动武形态”。从旁观者角度看,许崇灏如此失态,想必与汪氏积怨已深。
黄奋生听汪安之讲述以上情况后,建议他回苏一段时间,汪安之则仍坚持错不在己,以为许氏“目标于双哥”,要去徐州找顾颉刚。10月18日,汪氏将日用之物寄存黄奋生家,买票回苏州一趟,再去徐州。其实,同一天,顾颉刚夫妇恰好从徐州返苏,次日抵达南京时,汪安之已到苏州。10月24日,汪安之去庆泰酱园买五香萝卜,以备旅行之需,并为顾颉刚买资生丸数两。结果25日打算去徐州前,打电话去顾家,才得知顾颉刚已经返回苏州。晚饭后,汪氏去文通书局,确悉顾氏已经返苏,“有病如前”,“以时间过晚,恐多扰其精神”,约明天再去晤谈,因病延迟一天。《顾颉刚日记》1947年10月27日有“汪安之来”四字记录,汪安之记述甚简明:
晚晨去顾家花园,面致双哥会中情形,双哥病体尚未健全,因略述梗概。彼此同意,先期引退,余又以为光明磊落,此其时矣。……下午五时左右,因书一函,快递黄君,告以上情,并托照顾存寄行李。
黄奋生回信挽留,希望他“继续努力会务,唯仍拟借江苏路八号小屋办公”,汪安之“当即决然拒绝”。之后,黄氏又来一函,汪氏坚持迁址后才愿回去工作。这场风波,以汪安之这位正直“打工人”离职而告终。
四、余声
离职风波过后,汪安之回到苏州,虽然与边疆学会脱离关系,癔症却有加重的趋势。《日记》第四册中,有很多疑神疑鬼的记录,妹妹与外人搭话,他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骚扰;他去沧浪亭图书馆看书,有一老太说了一句话,他听见后,认为对他进行攻击,报警处理;有人敲门问询,他误以为是许公武从南京派人来骚扰他,不许他写日记等等,让人觉得他已走火入魔。顾颉刚也不再出现于他日记中,而《顾颉刚日记》中偶尔会提及他,如1948年2月22日“到汪安之处,听其与诸妹互诋”,正是汪安之发神经病后,与妹妹们争吵的真实写照。
建国以后,顾颉刚回苏州时,还会惦记有病表弟,如1950年6月23日有“雇车到汪安之处,未晤”及“汪安之来”的记录;1951年10月5日回苏州,8日“出遇汪安之”,12日有“汪安之来”的记录,还不时给汪氏写信。后来,因发病与邻居发生矛盾,苏州住不下去,汪安之一度北上,依其定居天津的妹妹生活,1955年6月26日曾去北京看望顾颉刚,同年8月10日又进京,顾颉刚在日记中提到:
安之表弟犯神经病,到处与人吵架,以致苏州不能住而移天津,又致天津不能住而移北京。适值回乡运动,派出所不任其迁入,又到毛主席处及人民法院告状。采龄妹自与东北张君结婚后住津。嵩龄妹任盘门外小学教师,每晨四时即出,每日来回走十里路,其工作精神甚好,惜有便血、头晕等病。寿龄妹主家务,子宫生瘤,小便不畅。此次来京,主于医治。此三表妹均肯工作,而二人不嫁,一人嫁而无子。安之年已五十,亦不结婚,只会胡闹,可厌之至!
彼时汪安之已经五十八岁,依然单身,固然可怜,但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顾颉刚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汪安之,是1956年4月28日,“汪安之自天津来”,并附记:
安之表弟患精神病,到处疑人与之为难,住天津久,与比邻崔家斗殴,欲居北京,来与予商。北京有何空房,且报进户口亦属不可能,只得遣去。
汪安之进京定居的想法,自然未能实现,此后如何收场,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悬念。
还有一事需要补充,汪安之虽患病,日记却未荒废。前几年,坊间出现一批无锡荡口殷家老宅中散出的古籍,我偶然在一旧书店见到日记稿本一册,看其字迹甚为熟悉,一时想不起来,回家后恍然大悟,那是汪安之1950年代的日记。过了段时间再去询问,获悉已被售去。后来,我去钮家巷文学山房旧书店小坐,江澄波丈告诉我,不久前买到一本苏州人的佚名日记,后来查了一下,作者是顾颉刚的表弟汪某。我想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却也没有向江丈索阅此稿,不知是否仍在文学山房,抑或早已转让。人生遇与不遇,都是巧合,一切还是顺其自然为好。